每个人都在寻找知心话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09-07 00:00 来源: 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 ■张光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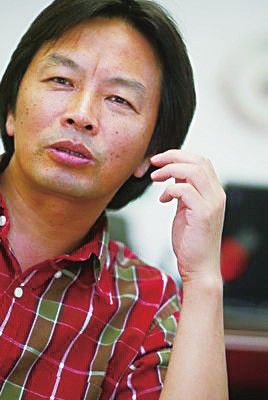 |
李敬泽:"读《一句顶一万句》,常想到《水浒》,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如此奔走,这种眼光是中国小说的'国风','国风'久不作矣。"
《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试图探寻人生的终极意义。
在看这部小说的时候,分明感觉到历史并没有在时间中化为灰烬或者掌故,那些八九十年前的往事、情绪与感受,依旧那么锐利和深刻。
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杨百顺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杨百顺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乃至于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纾解仇恨、化解矛盾、激发情欲有关。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的命运都是这样。
较以前的作品,小说关注的人物更为大众,叙述的故事更为“鸡零狗碎”。小说中有个细节值得关注,即两个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头上都戴着“绿帽子”,他们发现“绿帽子”只是个表象,看似是男女间的事,根子却不在这里,而是因为他们跟他们的老婆之间没话,老婆与给他戴“绿帽子”的人,倒能说到一起。偷汉子的女人和奸夫,话语如滔滔江水。说了一夜,还不停歇:“咱再说些别的?”“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从有话无话的角度讲,给他戴“绿帽子”的两个人,做得倒是对的。自己的“绿帽子”,原来是自个儿缝制的。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从腰里拔出刀子,又掖了回去。这是他们与武大他兄弟等人的区别,也是他们离开故土和亲族,出门流浪和漂泊的原因。他们身上似乎有阿Q的气质,但又没有阿Q那般执着与赖皮。
通读小说,杨百顺和牛建国都在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朋友呢?其实,我觉得,朋友的多寡,要看“朋友”的标准是什么。人分这么几种:不认识,认识,熟人,朋友,知心朋友。“朋友”的判断,就像《一句顶一万句》开篇写的:不在当面的表白,而是背后说起朋友的时候,是否提到过你。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你把别人当成了朋友,别人并没拿你当朋友。另一个判断朋友的标准是,在你走投无路时,你想投奔的人,和你能投奔的人,到底有几个。
阅读中,感觉到刘震云的这部小说,摆脱了此前《手机》和《我叫刘跃进》这两部与影视密切结合的方式,在将故事拉回到故乡延津的同时,作家重返当年创作《一腔废话》的路径,在小说中展开对话语的思考。整部小说写得从容不迫,作家一笔一划写了卖豆腐的老杨,铁匠铺的老李,赶大车的老马,剃头的老裴,天主教牧师老詹,这些最普通的乡里乡亲的事儿,喊丧的罗长礼是老杨的儿子杨百顺的偶像,但种种机缘使他的人生像滚铁环一样,没有按照他的希望走下去,而一件件看似无关的小事却一步步左右着他的命运,波澜不惊的生活让人寸断肝肠。
刘震云的书名,都是怪怪的。如过去的《一地鸡毛》、《一腔废话》、《温故一九四二》,都不按常理出牌。如今又弄出一本《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一万句”这话不是刘震云说的,是1966年林彪说的,作家事隔43年重新提起,并不是为了向林彪致意,而是觉得这话不同寻常,是一句知心话。为此,刘震云曾解释说:“我说的这句顶一万句的话,并不是一句深刻的哲理,而是朋友间一句家常的话,一句温暖和知心的话。这话本来知道,无非世事繁杂,忘记的时间太久了。突然听朋友说起,不禁泪流满面。”
找到知心朋友不易,找到“知心话”同样不易。刘震云说:“这一句话,大家可以读的时候自己找一找。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小说)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在找‘这一句话’。”
寻找话语的过程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灵魂,也使这部貌似写实风格的小说洋溢出很强的寓言色彩,平实的故事背后的理变得很“拧巴”。而这“拧巴”并未降低小说的质素,却使其意蕴获得一种飞扬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