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足经济学:经济不应以稀缺为核心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6-28 18:03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充足经济学
追求无尽增长的危害
在《出埃及记》中,饥饿的以色列人抱怨吃不到肉,耶和华便让天上降下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的“吗哪”,要求犹太人按饭量收取,并且不许留到早晨,留到早晨就会生虫变臭。在犹太人逃离的埃及,谷物堆在了巨大的谷仓里,属于法老的财富被保存起来。但在沙漠这种新的环境下,上帝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经济模型:只收取足够吃的东西。经济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和他的儿子、哲学家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就想建立一门“充足经济学”,父子二人合著了《多少算足够?》一书。
书中说,1930年,凯恩斯在《我们子孙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想象了这样一个世界:人们每周只工作15个小时,跟每周工作三四十个小时的时候挣的钱一样多,甚至更多,因为劳动果实分配得更均等。醒着时的闲暇时间远远多过工作的时间。凯恩斯这篇文章的主题很简单——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满足其需求所需的劳动时间越来越少,最后他们几乎无需工作。届时,人们将面临如何使用自由、度过闲暇的问题。凯恩斯在文中讨论的问题是:财富的用途是什么?过上幸福的生活需要多少钱?“挣钱本身不会是目的。说自己的人生目的是挣越来越多的钱就像说吃的目的是变得越来越胖。对社会来说也一样。挣钱不会是人永远的活动,原因很简单,钱除了花掉别无其他用途。我们不可能一直花钱,到某个时候我们会感到厌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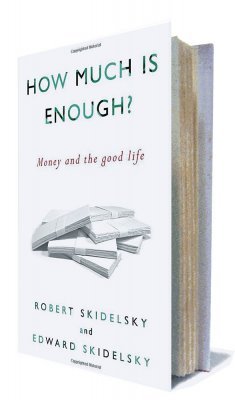
经济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与他的儿子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合著的《多少算足够?》
在斯基德尔斯基父子看来,凯恩斯想象的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对一个经济制度来说,资本不再积累时它就不是资本主义了。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动力基础是人类喜欢挣钱、热爱钱的本能。而随着充足时代的到来,这一动力将失去社会的认可,当任务完成后资本主义也就消灭了自身。但由于我们习惯了认为稀缺是常态,所以很少有人考虑过在一个物质充足的世界流行什么样的动机和行为准则。
凯恩斯说,大约100年后人类就能够达到富足状态,即2030年。但为什么凯恩斯的预言失败了呢?为何差不多100年过去了,我们仍在辛苦地工作?斯基德尔斯基父子认为,答案是,自由市场经济既给了工人决定劳动时间的权利,又激发了我们竞争、地位消费的先天倾向。西方文明跟魔鬼做交易,换到了无尽的知识、力量和快乐。我们实现了富足,资本主义令我们养成的习惯却使我们没有能力享受富足。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命运呢?必须吸取前现代的东西方智慧,恢复旧的被忽视和扭曲的幸福观。古典、中世纪和东方哲学认为,幸福生活不是保证我们会感到快乐的生活,而是与环境和谐共存、能在环境中自由行动的生活。幸福经济学把幸福看做满足,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幸福是性格、谨慎、行为和环境之间的和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依赖于能做出正确判断的性格。幸福还依赖于充足的闲暇。由此斯基德尔斯基父子提出,要回到凯恩斯和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在《懒惰的权利》中提出的闲暇论。
批评者说,增长不仅没有使我们变得更幸福,对环境也有灾难性影响。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但都没有更深入地反对无止境的增长。找出增长破坏幸福和环境的事例,对手可以反驳说增长没有破坏幸福和环境。但在科学家和统计学家告知我们之前,我们就知道对财富无止境的追求是疯狂的。
有人说,现在不是谈论终止增长的时候。如果凯恩斯还活着,他也会催促我们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以降低失业率和偿还国债。但我们需要区分短期内恢复经济的政策与实现幸福的长期政策,不能让当前的需要遮蔽我们的最终目标。另外终止经济增长的要求还有区域限制,不是说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应该满足于他们现有的生活水平,而是针对已经具备幸福的物质条件的地区。如果发展中国家继续发展,最终它们也会面对同样的困境,可以提前做好准备,不能重复西方的错误。
美国人会认为终止经济发展会阻碍创新,使大部分人处于懒散状态,反映了年迈的欧洲人颓废的思维方式。斯基德尔斯基父子解释说:“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人们有更多的闲暇,而闲暇跟闲散完全相反。”闲暇是没有内在目的的活动,是康德所说的“无目的而合目的”的活动。雕塑家在大理石上雕刻,老师教授一个高深的思想,作曲家努力写出一首曲子,科学家探索时空的奥秘——这些人除了做好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别无其他目的。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付出而获得收入,但激励他们的不是收入。他们在休闲,而非打工。他们的活动不是出于必需,而是出于爱好,是自发的,而非被迫的、机械的,告别打工之后闲暇才开始。我们想象力变得贫乏了,才认为所有的创造和创新活动需要金钱刺激。
闲暇的真意
有人可能会说,拿掉外在刺激,不会带来更多的闲暇。“懒人做什么事都离不开金钱刺激。没有金钱刺激,我们天生的惰性就会占上风,使我们感到无聊,患上神经机能病,酗酒。读几部俄国小说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要驳斥这种说法,只能诉诸信念了:如果工业的最终目的是懒散,如果我们劳动和创造只是为了我们的后辈能够终日舒舒服服地看电视,那么如奥威尔所说,所有的进步都只是“疯狂的奋斗,通向我们希望和祈祷永远不要实现的目标”。我们驱使自己不停地做事不是因为我们认为那些事情值得做,而是因为不管多么无意义的事情都比没事可干好。我们必须相信真正的闲暇的可能性,不然我们的处境就太令人绝望了。
另一个反思给了我们一些希望。人天生懒惰,只有收获的前景能刺激他们去行动——人的这种形象是现代独有的。经济学家们把人类看做驮东西的牲口,干什么事都需要胡萝卜或大棒的激发。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说人类面临的问题是,用最小的努力最大地满足需求。古代人不这么看。“雅典和罗马的公民虽然在经济上生产效率不高,但积极地从事政治、军事、哲学和文学活动。为什么不以他们而是以驴子当做我们的榜样?”
我们不能期望一个被迫、机械地使用时间的社会一夜之间就变得自由。但我们不能怀疑其可能性。罗素曾经写道:“有一些闲暇会令人感到愉快,但如果每天只需工作4小时,人们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现代世界确实是如此,这是我们的文明遭受的谴责,以前不是这样。曾经人们有轻松度日、玩耍的能力,这些能力如今已经被效率崇拜抑制了。城市人口的快乐大部分是被动的:看电影、看足球赛、听广播等等。他们积极的能量全部被工作消耗了,如果有更多闲暇,他们还会再次积极地享受快乐。”由于休闲失去了其自发活动的真意,退化成了被动的消耗,我们便把工作当成两种恶中较小的一个。波德莱尔在《私密日记》中写道:“人必须工作,不是出于趣味,至少是出于绝望,因为工作不像享乐那样无聊。”
斯基德尔斯基父子认为,现代经济学已经成了人们实现幸福生活的障碍。一本教科书说,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选择用有限、稀缺的资源满足无限的需求”。但经济学家哈里·约翰逊1960年就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社会,但仍然在许多方面坚持像生活在贫困社会一样思考和行动。”贫困视角和不惜一切地强调效率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曾经并非如此。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认为,我们天生对进步的渴望最终会超越自然与制度的限制。凯恩斯的老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幸福的物质前提,这一定义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把财富当做手段的观念。在马歇尔之后,经济学发生了转变。莱昂内尔·罗宾斯说,经济学“研究目的与稀缺的手段之下的人类行为”。这一定义把稀缺置于经济学的中心,且悬隔了价值判断。经济学研究的是实现目的的高效手段,对于那些目的经济学家们并不发言。但我们应该相对于需求而非欲求来考虑稀缺。有三套房子的人的生活一点也不窘迫,不管他多么想拥有第四套房子。我们说他的房子足够了,足够满足他的需求量。我们原则上都能够把欲求限制为需求,问题是一个强调竞争、货币化的经济逼迫我们欲求更多。经济学家关切的稀缺是这种压力人为制造出来的。相对于需求来说,我们的状态不是稀缺,而是极大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