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植被生态学家张新时:林里林外皆功夫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09-18 06:45 来源: 中国经济网
 |
 |
野外植被考察多在人迹罕至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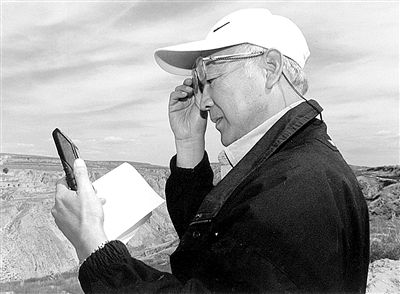 |
张新时说,野外考察苦是苦,但很有意思。
 |
张新时的妻子慈龙骏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很多理解与支持。
 |
保护植被是张新时须臾不忘的责任。
张新时,生态学家。原籍山东高唐。1951年至1952年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1952年至1955年北京林学院森林系本科毕业。1980年至198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生态学与系统学系攻读并获博士学位。1986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1990年至1998年任植物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长期从事植被生态学研究,揭示了我国荒漠区植被地带性分布规律,提出关于青藏高原植被在“高原地带性”与高原对中国植被地带分布作用的重要论点,提出了较完善与规律性的中国山地植被垂直带系统与类型,发展群落生态分析系统并提出了信息生态学的概念与结构,对现代生态学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采用信息科学先进手段与理论将中国“气候―植被关系”与全球生态学的研究推进到国际先进水平。参编《中国植被》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青藏高原植被研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毛乌素沙地乔灌木沙地质量评价》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新疆植被及其利用》获中科院科技成果一等奖;担任《中国植被图1:100万》副主编、主编。
1951年,18岁的张新时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农业大学的森林系。这一选择,纯粹是浪漫使然。那时候的张新时,喜欢文学,爱读小说。在他心目中,绿色很美,森林很浪漫。
此后的60年,跋山涉水,风雨兼程,青丝渐成白发。和60年前一样,森林始终浪漫美好。和60年前不同,他的科研中又增加了草地、荒漠、高山植被。植被是他读不完的书,行不完的路,丢不掉的责任。
林外之见
“我曾告诉学生,功夫在林外。学林业的人,不能只是‘就林论林’。自然界是很复杂的,我们要知道天上的事,比如气象;要懂得地下的事,比如地理地质;还要知道水里的事,比如要研究水土保持就要懂得水文知识。如果对交叉学科认识不够,基础打得不牢靠,研究就只能是点皮毛,搞出来的东西也一定是浅薄的。”
在科研中,张新时始终强调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重要性。数学是定量研究的基础,也是张新时最为看重的“林外”功课之一。尽管大学时代的数学成绩还不错,他依然觉得不足,计算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遗憾。1979年,张新时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计算机在美国刚刚兴起,张新时敏锐地意识到,计算机将是进行定量研究和数量分析的有力工具。于是,张新时开始刻苦学习计算机课程。张新时记得,那时候,康奈尔大学的计算机教室只在每天黎明时分关闭两个小时,他就从早到晚一直泡在里面,常常熬整个通宵。年逾不惑的张新时凭借顽强的毅力过了计算机这一关,此后,计算机成为张新时最好的工具和帮手,也让他在“数字地球”时代走在了国内数量生态学研究的前沿。
1986年,张新时博士毕业回国,来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开始从事数量生态学的研究。他率先进行植被—气候关系的数量分析研究,并在国内率先开展全球变化生态学的研究,其植被研究也率先进入数字时代。1995年,张新时担任中国植被图(1:1000000)项目负责人。在国土如此广阔、自然条件和植被如此复杂的国家编制百万分之一比例尺植被图,是一项浩大而艰辛的工程。如何让这份重要的地图更好地服务于科研和社会建设?张新时力排众议,决定同时出版建立在数字化成果基础上的印刷版和电子版。2007年,历经10余年的呕心沥血之作《中国植被图》(1:1000000)出版,数字化地图的优势立时显现:读者可以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在电脑上进行任意的拼接、剪裁、加注记,还可以对图中各个要素进行检索、提取、数理统计、多元分析,或者用数学模型进行计算,重新生成各类图件。“不仅如此,数字化地图还可以实时更新植被类型及其分布的空间等数据资料,这样就极大地扩展了植被图的功能。”张新时自豪地介绍说。中国植被图(1:1000000)是一套近10公斤重的“大部头”。这些内容变成电子版,一张光盘的容量就可以解决。印刷版的《中国植被图(1:1000000)》标价不菲,为方便学生使用,张新时将中国植被图的电子版象征性地定价为1元(仅对大学学生)。
(责任编辑:马常艳)
关注气候这个“林外”因素与植被的关系,使张新时收获了一项新颖的成果。这项成果的缘起,是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在这篇报告文学中,作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周恩来总理询问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正是处在回归沙漠带上,还保留着这么好的热带雨林,这是为什么?蔡希陶回答说,这是因为西双版纳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从太平洋、印度洋吹来的两股季风汇集在这里,带来了充足的阳光和雨水。蔡希陶的解释没有说服张新时。长期以来,专家们将这类植被地理学特殊现象的原因,都归结于季风的作用、离海洋的距离或山脉的雨影作用等,并没有从根源上进行探究。
张新时将目光投向了青藏高原。根据当时(上世纪70年代)气象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他认为青藏高原的隆起是导致植被地带演变格局的根本原因。青藏高原的隆起改变了大气环流格局,从而导致了斜跨欧亚、北非大陆中部的地球上最广阔的干旱地带,也带来了大陆两翼植被地带序列的不对应现象。因此,在东亚大陆,其荒漠地带在纬度上明显向北上移了大约10°至15°,成为温带性质;在地球其他大陆上是干旱荒漠或稀树草原的亚热带,在东亚却分布着特有的常绿阔叶林植被,形成了“回归沙漠带中的绿洲”。
这一新发现引起的兴奋燃烧着张新时。经过3个不眠之夜,张新时将他的观点写成论文。同年(1978年),他将这篇论文提交给了全国植物学会。此后,他又用英文改写了这篇论文,寄给了美国的《密苏里植物园年报》。该刊物的审稿者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古生物学家,他不同意张新时的全新观点,认为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青藏高原隆起之前是潮湿的森林,并以长江流域一种大叶子植物的化石作为证据。张新时则从中国科学院古植物专家徐仁院士那里获得一些证据,证明这一地区当时可能是干旱地带。张新时坚持自己的观点,宁愿被退稿也不修改观点。不久,该刊物一字未改地发表了他的论文。
苦中之乐
1955年,张新时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新疆农学院工作。在新疆的23年间,他基本上是在野外考察和文献研究中度过的。他说,“我喜欢在外面跑。搞植被研究不能靠在屋子里冥思苦想。野外实地考察是科学发现的源泉。”踏遍了新疆的山山水水之后,张新时发现“森林是不够搞的”,原因是新疆大部分地区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天然森林的覆盖还不到1%。在研究森林的同时,他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纷繁的高山植被、广阔的草地和荒漠。
野外植被考察多在人迹罕至之处,很多地方不通汽车,只能骑马或骑毛驴,或者徒手攀爬,遇到泥石流、塌方是常事。搞植被研究,需要采集大量的标本,还必须保证标本完好。张新时和同事们白天忙于考察,晚上也没法睡安稳觉,需要每晚给标本“翻身”,防止标本腐烂。如果碰上雨天,经常彻夜难眠。
那20多年间,张新时走遍了天山的东西南北,以及昆仑山和阿尔泰山。“野外考察难免有意外发生。苦是苦,但很有意思,看到新的东西,并且能找到和揭示出本质,就非常有意思、非常快乐了!”张新时这样描述野外考察的苦与乐。
乐从苦中来,乐从发现中来。1957年,张新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新疆综合科学考察,同行的还有来自前苏联的专家,他的植物生态学从此起步,俄语水平也迅速提高。经过一个夏天的考察,张新时已经可以临时充当考察队的俄语翻译了。熟练的俄语给张新时打开了宽阔的视野——当时关于新疆植被和自然环境方面的资料,大多来自俄语文献。根据这次科考的成果,张新时在1959年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论述了天山森林的地理分布规律。
1963年暑假,张新时再次踏上天山科考之路。这次考察历时40多天,对伊犁地区的新源野果林林区进行了地植物学调查。在此之前,关于野果林的地植物学研究少之又少。张新时惊喜地发现,野果林中有完美的植物群落。“野苹果以伞盖般的树冠投下柔和的绿荫,阳光透过苹果树叶洒落下来,很多的林下植物都在争取阳光,很神奇的是,每一片叶子都不会重叠,都能得到阳光。密密匝匝的镶嵌类植物完全铺满了大地,根本看不到土壤的颜色。这是大自然的杰作。”
在荒漠地带山地,常见的植被类型是针叶林,伊犁野果林这种阔叶林实属罕见。通过实地考察和查阅资料,张新时认为,伊犁野果林是中亚第三纪残遗阔叶树种与更新世的北方“移民”的结合物,是经过充分改造与适应过程的“残遗”群落。野果林所占据的地境,是伊犁谷地中最为温和、适宜和具有“海洋性”气候特色的地段。此外,伊犁地区的前山由于未遭受到第三纪末—第四纪初冰期山地冰川迭次下降的侵袭,又较少蒙受间冰期和冰后期荒漠干旱气候的影响,遂成为喜暖中生阔叶树的“避难所”。此后,几乎所有研究伊犁野果林的文章,都会提到张新时的这篇《伊犁野果林的生态地理特征和群落学问题》。在自己众多的论文、专著中,张新时偏爱这篇“小”文章,不仅因为是他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植物群落样本并给予科学的解释,更因为这是一篇对大自然精美造物完美而透彻的记述。然而50年后,当他再次站在伊犁野果林中,昔日的“伊甸园”已遭破坏,痛失乐园令他满怀悲凉。
在数不胜数的科学考察中,对张新时影响最大的,是1973年到1976年的青藏高原科考。这次科考由来自不同学科的数百位科研人员参加,其丰硕的考察成果成为迄今为止研究青藏高原植被的权威资料。通过这次考察,张新时对青藏高原植被分布、类型及与地理因素的关系有了全面深入的规律性认识。1978年,张新时发表了《西藏植被的高原地带性》一文。他在文中提出,西藏高原的植被不同于一般的“水平地带”植被,也不同于山地的“垂直带”植被,它属于“准平原式”的垂直带植被,可称之为“高原地带”植被。西藏植被的成带现象自东南向西北依次变化:森林—草甸—草原—荒漠。这些高原地带性的形成主要取决于高原巨大幅度的隆升及其所引起的特殊的大气环流状况。潮湿的西南季风乃是西藏东南部热带和亚热带山地森林发育的基本因素。高原面处在西风环流和“青藏高压”控制下,在这种大陆性高原的气候条件下,形成了高寒草甸、草原和荒漠植被。
责任之辩
在60年的科学生涯中,张新时几乎踏遍了我国主要的林区和牧区。足迹所至,不乏大自然鬼斧神工般绝美,这样的美令他心旷神怡。在张新时的记忆中,野果林是“人间仙境、绝美之处”。“野苹果一般在5月初开始放花,花开时漫山粉雪香海”,“群落的外貌十分美丽,在天山苹果淡绿色球形树丛的背景上,高耸起山杨挺拔的青白色树干支撑着圆叶闪烁的树冠,间以几株墨绿色的尖塔形云杉,构成稀疏的上林层。”在张新时的论文中,有着充满诗意的文字。
足迹所至,也有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如何以科学的方法保护脆弱的生态,成为张新时的责任所在。为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直抒胸臆,撰写文章,不畏批评和质疑。为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奔走呼吁,甚至与同行和朋友在会议上公开辩论、交锋。
面对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有的学者强调应以自然恢复为主,提出从人工建设转向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张新时不以为然。他认为,“把生态重建的责任推诿给自然去旷日持久地恢复,是不负责任和不作为,也有悖于‘谁破坏,谁补偿;谁污染,谁治理;谁享用,谁埋单’的全球环保公理和生态伦理观念。”他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植被图数字化平台耦合的建设、植被全球变化的数学模型和关于草原生产方式的研究,是目前张新时最为注重的领域。针对我国草原普遍发生退化的现状,他认为,“退牧还草”虽是积极的办法,但还必须解决畜群的饲草和牧民的生计。他提出,我国天然草地的功能应转向以发挥生态效益为主,草地畜牧业必须从数千年传统、落后和粗放的放牧方式,全面地转向以人工饲草基地为基础的现代化舍饲畜牧业先进生产方式,而不仅仅是简单的“退牧还草”和“轮牧”。
无论是频繁的野外考察,还是对科学问题的深入思考,张新时都得到了妻子慈龙骏的理解和支持。他深情地回忆道,50多年前,年轻美丽的慈龙骏在北京林业学院毕业后,放弃了留苏或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到新疆与他会合。他们在新疆安家,并养育了3个子女。慈龙骏的研究专业是荒漠治理,不仅与张新时有许多共同语言,更给予了张新时无私的支持。一次,慈龙骏因重病住院,张新时要去西藏科考,慈龙骏忍痛鼓励犹豫难舍的张新时按时出行。慈龙骏走遍了新疆风沙最严重的40多个县、100多个乡,获得了一系列成果。对于妻子的坚韧,张新时心生佩服:“她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博士时都45岁了,还有两个上学的孩子需要她照顾。她很有毅力,非常勤奋。她的主要课程考试成绩都是A。”为了通过严格的论文答辩,慈龙骏几乎不眠不休,26天都没有上床休息。经过多年艰苦的工作,慈龙骏成为我国著名的荒漠化防治专家。她领导的研究小组在新疆创建了以“窄林带、小网格”为核心,灌草带、防沙林带与护田林网“三位一体”的防护林体系。采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专家系统创建的沙地土地利用分类与荒漠化评价系统,通过建立“三圈”模式,完善了防治荒漠化工程的理论与技术体系。
并肩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的张新时与慈龙骏,都已年过七旬,在工作中依然一丝不苟、精神焕发。
(责任编辑:马常艳)